2024年05月30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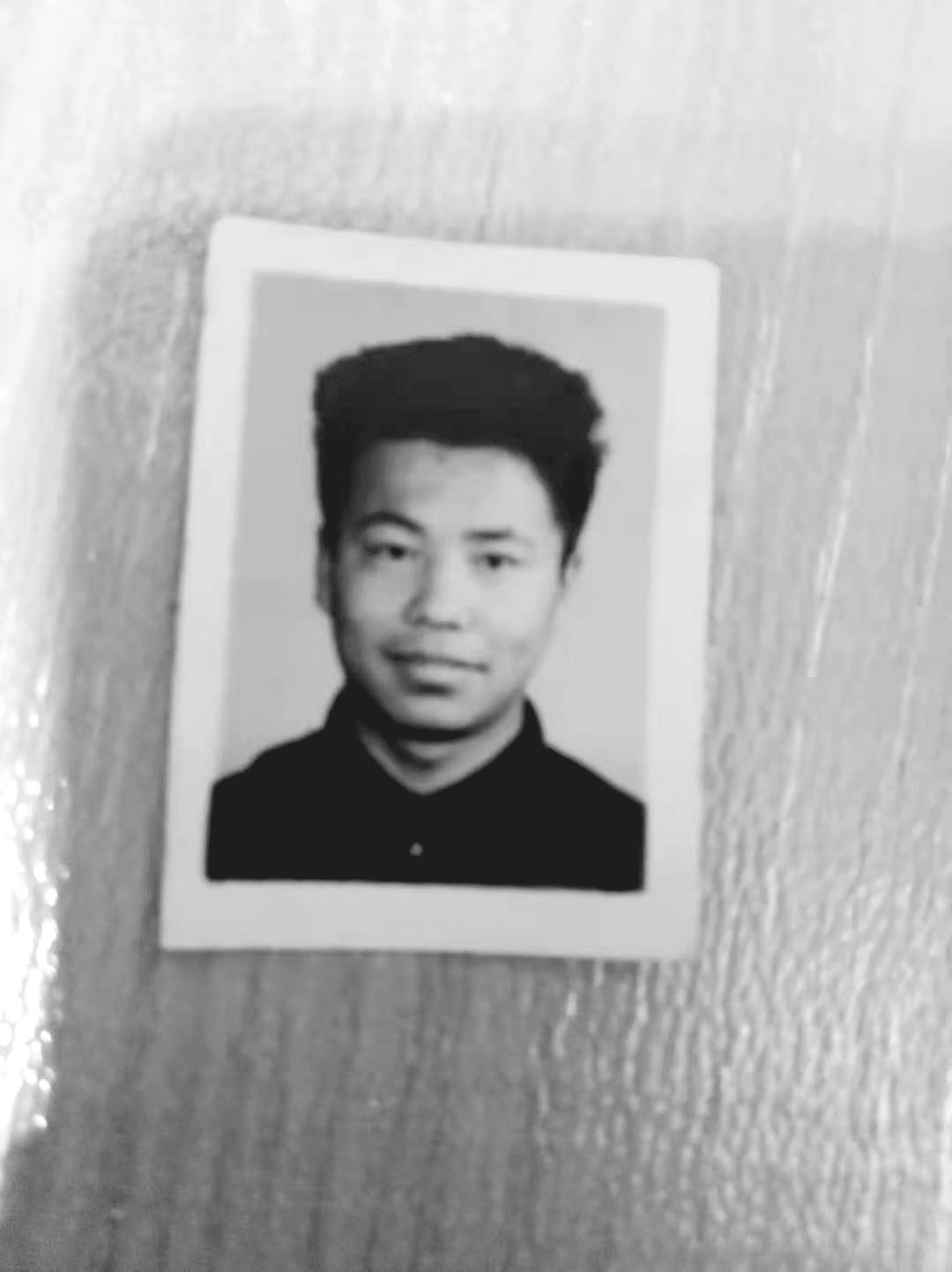
旧物,是剩余在生命里的温暖。循着时光的轨迹,这温暖就像春天的阳光,普照万物又关乎心灵。即便是一张旧照片,它留存的时光,也会以宁静的手势,抚慰我们的心灵。
进高中同学群后,没过10分钟,就有一个网名叫小老大的同学发到群里一张寸照,是用手机重新拍下来的一张黑白寸照。我好奇地点开放大,仔细一看,竟然是当年高中时代的我。疯长的寸头,如同戴上了一顶黑色的礼帽,脑袋显得很大,脸上满是未曾褪去的青涩。
这张寸照,记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的高中毕业证上,所以,我一眼就从寸照上认出了当年青涩的自己。
那应该是1983年六七月间,寸照拍摄于高中毕业前夕,距今近40年了。可是这张寸照依然色泽明亮、黑白分明,可谓历经沧桑终不改,洗尽铅华呈素姿。恍惚间,我好像又回到了难忘的高中生活。
一间宿舍,上下铺,挤挤巴巴,30多号人。那时,我与王景富有过很深的接触。读初中时,王景富在我心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他语文好,作文很棒,我非常佩服他。上高中,我们一个班又同住一间寝室。不久,教语文的马猛老师就发现了这棵苗子。课堂上,经常提问他,还经常给我们读他的作文。我们很谈得来,我的摘抄本就是从接触他以后建立的。他有惊人的记忆力,我经常逼他口述名言警句,当时我积累了好几本。实事求是地说,如果与王景富没有这样一种接触,也许我的摘抄和后来剪报的习惯不会养成。
在任民镇高中,我第一次接触文学刊物,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现代文学作品。那天,在任民镇老姨家,见到一本《上海文学》(1981年6月号)。丛正里的报告文学《美的心灵》,感情真挚,催人泪下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涉猎各种文学刊物。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我认识了著名作家王蒙;在《北方文学》上,我认识了青年女作家张抗抗;在《青年科学》上,我认识了科普作家叶永烈。我开始订刊物了,我开始买《唐宋诗选》,我也开始学着同班同学侯铁良的样子,凑一些乱七八糟的顺口溜。
高一下半年,我的视力逐渐下降,黑板上的字,越来越看不清楚了。上课,我常常是凭着听觉听课,课下再借笔记整理老师的讲课内容。初中时,我平面几何学得比较好,到高中学立体几何,一点儿不感到吃力。教数学的于德仁老师对我挺好,课堂上总提问我。我解立体几何题的能力很强,无论需做多少辅助线的难题,我不用动笔,不画图,就能口述解题步骤。当时的同桌吕东武(现在也是老师)现在提及我,都一个劲儿地竖大拇指,说我是数学通。
1982年7月,念完高一,任民高中被“砍了”。我们这些人兵分三路:分安达五中一部分,分一中一部分,分育才一部分。
初到育才高中,班主任王杰新老师就很看重我:语文科代表是我,数学科代表是我,班级学习委员是我。之所以分这么多差事给我,可能是因为高一学年考试成绩突出。
学生时代的我,课堂上表现总是很主动,爱发言,无拘无束。有别的老师听课,许多学习好的学生怕答错,我不会,就连没准备好的问题,我都会勇敢地举起手。因而,无论上什么课,我都是课堂上的“主角”,我也因此得到了比别的学生更多的锻炼机会。现在,自己当了老师,我也喜欢那些发言积极的学生。
语文和数学,我对数学科最有感情,不只因为数学老师对我格外地好。现在,我也对数学非常有感情,见到难一点儿的题,总要抄下来,拿到家里死抠。读高二时的数学老师叫王晓光,也许是我当时对数学科的痴迷表现,引起了他对我格外的注意。
王老师大学毕业刚来校工作那会儿,他的课讲得不是很明白,但他有许多课外书,他
张林
的那些课外书深深地吸引了我,只要一有空儿,我便和王老师泡在一起,抠那些难题,抠那些偏题,抠那些怪题。那时,我所接触的数学知识超出了老师讲的范畴。
爱屋及乌。我对于数学科的偏爱,也增进了我和王老师的感情。王老师刚来时,个别老师和一些学生都“欺生”,唯我愿意亲近他,我们在一起平等地交流。我对数学方面的“深究”,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,有时连我都觉得自己有些过分,爱钻牛犄角,然而,我从来看不出王老师有什么不耐烦。
王老师的穿戴,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平时授课,他常穿一件深棕色中山装,板板正正,走起路来,腰杆绷直,有学者风度,有绅士派头。每次见到,我在心底就萌生一个热望:等毕业了,有了钱,也买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装穿穿。后来,回乡教书,我买的第一件上衣就是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装。现在,若问我喜欢啥颜色,我会毫不犹豫地说:棕色。当初结婚做家具,海龙二哥问涂啥色,我说涂棕色。一位老师,一位很有特点的老师,对学生的影响很大,他的一言一行,他举手投足,有时能影响学生的一生。
对数学科的偏爱,我得到过成功的回报。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数学竞赛中,我荣获过一等奖。奖品是几本数理化课外书。毕业参加工作已近40年,我散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书,但唯有这几本写字卡戳的书珍存至今。
在高二,数学科的学习,我花的精力最大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,这方面用的多了,那方面用的就少了。由于整日死抠数学,我荒废了本来基础挺好的其它学科。
在任民高中,刘希敏老师教外语。提到她,就让每个她教过的学生感动,她的耐心和敬业精神,那是有口皆碑的。高一时,我外语成绩还不错;到高二,换了其他老师教外语,对学生不是很有耐心,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被心爱的数学挤占了,我偏科了,我的外语成绩一落千丈。好心的外语老师“破天荒”地把我叫到办公室,郑重地跟我讲:你不能偏科。高考时,外语不行,数学再好也考不出去。可气的是:当时,我没拿老师的忠告当回事,我充耳不闻,依然我行我素。结果,吃亏的还是我。
成绩下来,我数学全校第二,90分(百分制),与第一名的杨孔林差1分,外语却只考了25分。一败涂地的我躲在家里,没脸见人,自食着偏科落选的苦果。高中,最为关键的二年,决定终生命运的二年,我没能把握住自己……
往事如烟,不堪回首。
四十年来,也有太多太大的变化。单说照相,当数码相机兴起,各种美图软件博得人们欢心时,再看这张黑白寸照,觉得它有浓厚的岁月感,真实而亲切。
当年高中毕业时,同学间互赠照片作为留念一节,我真的不记得了,更没想到这位同学如此珍重温暖如春的同窗情谊,当年的一张寸照,还保留这么久又这么完好。花甲之年的我,一时被感动得心潮涌动,几近流出眼泪。
其实,也正是无数让我感动的人和事,给了我跋山涉水的力量和战胜自己的信心,他们就在我的记忆里住着,随时提醒我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。
这世上,并不只有精致、新颖的事物才能博得人们的欢心和喜爱,有些物件,比如这张黑白寸照,在与人朝夕相伴的岁月里,对它的感情,早已由单纯的喜欢转化成留恋。情之所至,令人想起的这段旧时光,如一坛老酒,越放越醇香。